学术咨询服务正当时学报期刊咨询网是专业的学术咨询服务平台!
发布时间:2021-02-06 15:4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杜威(John Dewey)抵制原教旨的个人主义,宣称据此认定的个人自由意志是虚构的; 而关联性才是事实。 用他自己的话说:追究个人如何关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本来就生活在关联之中。 杜威的眼光是革命性的,与儒家角色伦理相呼应,他通过发展一种独特
摘要:杜威(John Dewey)抵制原教旨的个人主义,宣称据此认定的个人自由意志是虚构的; 而关联性才是事实。 用他自己的话说:“追究个人如何关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本来就生活在关联之中。 ”杜威的眼光是革命性的,与儒家角色伦理相呼应,他通过发展一种独特、稳定、关系造就人的习俗构想,使关联性这个人类生活事实具体化,并使之成为稳固的现实。 也就是说,他发展了一种独特而通俗的习惯性和“个体性”的话语来描述人类的多种关联模式,认为关联性能够增益人们的活动,并将简单的关系转变为交流互动的社群关系。
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杜威使用另一套话语重述了关联性是一个基本事实,以具体的人物角色而非独特的习俗来规定关联性在家庭和社群生活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即我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身份,如儿子、老师、祖母、邻居等。 对于儒家而言,这些身份角色不仅诠释了人们的关联性,而且由于家庭及社群中的角色都有相应的规范,从而指导人们采取与自己身份相符的适当行为。 对于儒家和杜威而言,单纯的关联性是给定的,而只有蓬勃兴旺的家庭和社群才能实现人类的最大成就。 我的论点是,儒家的“学以成人”概念,能够为当代西方哲学论述中杜威等早期哲学家以及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等新近哲学家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给出另一种阐释。
关键词:杜威 儒家角色伦理 个体性 关联性 学以成人 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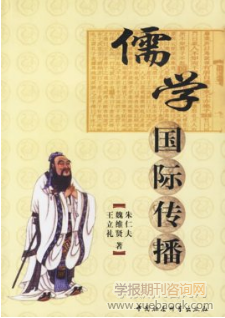
[美]安乐哲/著 黄田园/译 温海明/译审
一、问题铺垫:“智慧”今何在? [见英文版第4页,下同]
雄辩如毕达哥拉斯,将整体和实用的生活方式描述为哲学(philosophia)——“对智慧的爱”——固然有对抽象理论科学的深思,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还包括了基于人类灵魂不朽假设的宗教实践、定期禁欲修行、社会政治改革计划、持续道德反思、养生方法,甚至是饮食要求和禁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毕达哥拉斯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哲学理念却日渐式微,哲学之旅让位于迥然不同的朝圣之行,即对抽象、绝对知识及其必然性的追逐。 “知识”和“真理”成为系统哲学的词汇,而在西方学术长廊中,“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过时的名词。 对理论及精神抽象的过度推崇,意味着实践智慧、修辞学和美学已让位于盛行的二元论。 总而言之,哲学(philosophia,“对智慧的爱”)已演变成“知识论”(philoepisteme),即“对绝对知识的热爱”。
文学论文范例:儒家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建议
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这样阐释所谓“错置具体性谬误”:当形式上抽象的东西被认为是真实而具体的,错误的推理就产生了。 a怀特海推演了这种“致命病毒”的历史,认为其后果是会阻碍我们理解关系的内在性、建构性和创生性。 他指责伊壁鸠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没能意识到抽象化的危险性”,使得知识变得封闭、僵死,不再发展,实际上排除了获得智慧的可能性。 根据怀特海的说法,同这些哲学家相关的“思想史是由生机勃勃的开显和死气沉沉的闭合构成的悲剧性混合物。 确定了完满的知识,也就失去了洞察感。 这种教条主义是学习真知的敌人。 在完整而具体的事物关系网中,各关联事物的特征,影响着该关系网连接的整体特征”b。 这里怀特海所称被确定知识的假设冲抵的“洞察感”,指的是在独特个体之间建立实际联系的创造性思维的进步。 的确,创造性地思考事物之间最佳的关联,才是智慧的实质所在。
怀特海以“友谊”为例,认为这种关系是由相关联的两个人的独特性所构成的。 真正有意义的友谊的持续性具有强烈的揭示意义。 友谊最“具体”的意义便是友谊中的两个人最大程度的相互“欣赏”:他们相互放大和增加了彼此的分量。 更重要的是,这种重要关系的实现并不以牺牲任何一人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为代价,反而是产生促进个人独特性和完整性的有益结果。 完整性既意味着每个个体的持久特殊性,又意味着“合二为一”的友谊。 这既是真实关系的实质,也是宇宙意义的根源。 在这种收获性的友谊发展过程中,个人最终成为一种抽象概念,而人们共享的友谊则成为最真切具体的东西。 对关系的内在性、建构性、创生性的理解,就是怀特海所说的“审美”逻辑,而非“理性”秩序。 任何美学的实现都需要在所获得的全部成就效果中充分地展现具体的细节——比如友谊本身的“关联性”。 如果说“知识”是通过理性地认知抽象普世真理获得的,那么“智慧”则是从实用和审美的角度,通过和谐化具体的关系并优化其创造性而获得。 友谊中就存在真正的智慧。
怀特海严厉批评了古希腊美学忽视了个别细节与和谐秩序之间的必要平衡。
欣赏希腊艺术时,除了强制性的和谐,总还渴望寻找一些能体现顽强独立性的细节。 任何艺术形式的最典型范例,都达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平衡。 整体显示出部分,使每个组成部分都提高了自身的价值; 部分构成了整体,而整体超越却不破坏部分。 c
当应用到人类经验中时,人际关系的展现使家庭和社群变得有意义。 或者动态地说,关系的展现使这些关系成为“产生积极意义”的情境型案例。 而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强调抽象的一致性,则排除了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任何这样的关于和谐的理解都是真正威胁生命的。 正如怀特海所言,我们的生命是通过经验展示来呈现的。 一旦失去这种展示欲,我们就脱离了心灵的运行模式,逐渐下降到过去的平均水平。 等到与过去的平均水平完全一致,就意味着生命力的丧失。 剩下的不过是贫瘠的无机物质。 d
怀特海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和谐——实际上就是智慧——只能从生活细节的真实共享经验中产生。 因此,这种和谐的智慧永远是互联的,而不是单边的; 是互系的,而不是单一的; 是公开的,而不是封闭的。 智慧首先是具体的、局部的,然后才是抽象化的知识。
中国文化对此的叙述与古希腊的有所不同。 以儒家的训导“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为基础,中国哲学从早期就不断追求智慧的本土化,将人际关系中的个人修养提升为能显现宇宙意义的源泉。
儒家经典《大学》主张,只有通过致力于个人修养的方式,人们才能全面地理解知识和道德,最终改变世界。 这篇文献简练而全面,其中心思想是:尽管个人、家庭、社会、政治乃至宇宙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但一切皆必须以个人修养的提升为根本。 每个人对家庭、社群、政治都有独特的视角,并能够通过审慎的成长和表达,更加清晰地辨析自己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定位和关系,使其更具意义。 也就是说,自我培养、学会做人,就能够拓宽宇宙的意义; 反之,越来越有意义的宇宙又为个人修为提供了沃土。 这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分清本末。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大学》)出于个人修为和获得智慧的优先考量,我们应当阅读《中庸》和一些新近出土的楚简里面的论述,其中包括《道德经》《性自命出》《五行篇》。
二、提出问题:摒弃“生即为人”的观点 [7]
通过研究“成人意味着什么”这种常识性问题,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区分对抽象知识的追求与实践智慧的培养。 英语说“Everyone (or everybody) please stand up”(每个人,请站起来),现代汉语则说“大家请站起来”,后者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过程宇宙观。 “每个人”和“大家”这两种表达方式的鲜明对比通常是无意识的,却隐含了一种默认的根本差别:一方是个体化、独立的“生即为人”; 另一方则是情境关系中的“学以成人”,也就是通过在家庭和社群关系网中不断努力承担协作性、交互性身份角色,成长为独特的人。
以《荀子·子道》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则轶事为例,来对比“生即为人”体现的单向度个体性与在“大家庭”中“学以成人”所体现的相互关联性。 孔子哲学以“仁”为主题。 一次他让弟子分别阐述对“仁”的理解。 有学生认为这是一种利他主义,意为“爱人”。 孔子对这个答案不以为然。 另一位学生则认为这意味着设立一个行为标准,以“使人爱己”。 孔子评价说这个答案更好。 接下来轮到颜回应答了,颜回直截了当地指出“仁”的意思就是“爱己”。 孔子听了十分高兴。
当然,从独立的“生即为人”观来看,“自恋”很难算得上是一种美德。 但是这段文章的重点在于,从“学以成人”的相互关联观而言,“爱己”既不是只爱别人的利他主义,也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利己主义。 事实上,这种以“己”为内核的“仁爱”是双向的,体现的是内在关系,而不是外在关系; 是互构的关系,而不是偶然的接触。 “爱己”就是珍惜那些特定的人际关系,将其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源和基础——也就是在与配偶、孩子、学生和同事的关系中“爱己”。 在这种“学以成人”而不是“生即为人”的模型中,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家庭的兴旺是同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
《五行篇》与《孟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感知的关系,这使我们有机会更加明确地聚焦于“学以成人”这一概念。 我们需要再次反思长期以来对孟子学说的“先验”化误读——一种抽象的、天生的、不可或缺的人性观,在生活经验中得以实现的既定的天生潜能——从而确定这种“生即为人”的形而上学人性观是否与致力于“学以成人”的中国早期的宇宙观相一致。 a
三、从《五行篇》看《孟子》[8]
文献《五行篇》的问世时间似乎早于《孟子》,与《孟子》有明显的共鸣,并对后者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b《五行篇》中的五行(仁、义、礼、知、圣)和孟子人性观中的四端(仁、义、礼、知)之间有明显的顺序上的对应关系,然而这五种后天习得的习惯需要在家庭和社群中进行有效的互动才能养成,而孟子人性观中的四端是人类经验的初始条件,遵循四端又是我们道德修为的基础。 那么,如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呢?
在《人性与行为》一书中,杜威对将“人性”和“行为”截然分开来探讨的思路提出质疑,c他坚持认为养成的行为习惯本身就是自我圆成的要旨。 d同样,《五行篇》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极力主张将得体的行为理解为个人成长过程。 我的观点是,孟子的人性观远非一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天生观,人性应被域境化地理解为一直在受环境影响而不断改变的道德养成过程。 就是说,“大家庭”是培养贤人的环境,而培养出来的贤人则是家族光耀的成果体现。
在这个论述中,《五行篇》中强调“德”而非“性”是很重要的。 正如《五行篇》一开始所解释的那样,四种优秀的“德”——仁义礼智——是通过习惯化的过程习得与达致和谐的: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a 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b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 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c
《五行篇》的第一段强调“德”的培育,这可能是《孟子·离娄下》中做出类似陈述的原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五行篇》第一段的最后两行表明,要域境化而不是单向地解读《论语·述而》中的“天生德于予”。 就是说,我们在读《论语》这段话时,如果考虑到天人之间共生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可能会这样解读:“天”提供了一种传统背景,使人类的修身计划可以有效进行,可以说“继之者善”; 而人类良好习惯的形成与扩展,清晰地表达了“天道”。 我们可以通过“天”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认识并了解它们。
四、一个不同寻常的设想 [10]
思考孟子的人性观,首先要明确我们自己的预设。 康德(Kant)、洛克(Locke)和穆勒(Mill)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不断大力推广的强大哲学思想已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硬通货”,在这一传统下,许多汉学家对于孟子人性观的解读方式也深受影响。 自由主义关于“自我”认识的词汇——个人主义、自我意志、平等和自由——通常包含所谓人道主义的一套逻辑假设,即把学有所成和全能的个人从令人麻木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去追逐自我利益,以保证所谓民主的运转。 不受束缚的自由将使那些无拘无束、保持自然状态的个人得以“证明”自己是健康政治生活中的成熟参与者。 所谓自发性、独创性和天才人格的一套话语属于这样一种信念:不受约束的人类拥有与生俱来、应该充分发挥的天资。
这些设想由来已久。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根深蒂固的常识偏见深感担忧,坚持认为“我们对事物的基本思考方式是远古祖先的发现”d。 就是说,我们勉强接受了形上实在论作为一种共同常识,却发现西方语言中沉淀着一种不显著却广泛存在的普世观念,即将个别事物看作某一类别的个体“成员”。 而且由于这种普世性具现于个别事物中,我们的认知逻辑能够识别并掌握之,并可将知识对象命名为:个体性、特定性和一般性。 事实上,我们甚少这样有意识地分析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知识,往往只是当作日常经验中的惯有思维方式。 正是这种悠久的思维习惯才使得对人类进行定量地“个体化”理解符合常识。 时至今日,这类旧观念却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即便科学早已教会我们用不同方式来看待事物。 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物体间的关系性是绝对的,这与个体事物的内在特性无关,并且物体之间的关系性也没有必要通过内在性来加以表达”e。
五、个体化原则 [10]
从比较宇宙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辨析很重要。 我们如何理解“人性”的问题,只是如何看待在中华文化中进行“个体化”这一更大课题中的一个例子。 正如詹姆斯进一步评说的:“种类和同类——这一认识对于我们在众多思维途径中寻找出路非常有用! ”a毕竟,无论我们的文化背景和归属如何,只有通过个体化来理解事物,才可以完成最普通的日常事务。 在这里,我认为要讨论的是两种迥异的个体化策略之间的文化对比; 当然,这也相应地包括对支配着事物、种类、范畴、概念和理论的形成的文化假设进行的比较。
在最近的哲学讨论中,被放在语境和实践中去理解的概念,其单一语意的正当性已经受到质疑。 例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理解掌握一个概念不在于知道一个抽象的定义,而在于理解概念在思想和实践的具体片段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声称,定义一个概念,不需要通过具有封闭特性的一组特征,而是可以通过事物本身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来进行定义。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定量和定性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的“学以成人”的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早期的中国宇宙观而言,定量远非“事物”的客观情况,而是对事物具体关系性质的还原主义的简约化抽象(正如所谓专业、客观的说明只是对非专业的一般性描述的一种简单抽象)。 常识是我们提炼出来的智慧,但同时也可能会遮蔽我们的双眼。 威廉·詹姆斯警告说:“我请你们经常持有对常识的怀疑。 ”b
六、诠释语境:“气”的宇宙观 [11]
《孟子》中“气”的宇宙观反对那种单体外在关联的本体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认知者是独立且自足的,与外部“个体化”的认知对象相隔离。 相反,“气”的宇宙观源于经验的整体性,并将事物置于整体关系中。 儒家世界观,从起源到发展演变,从未提到过自由主义中利己、现成的个人概念。 对儒家孟子而言,由消极自由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脱节,不仅不能造就人,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倒退。 借用杜威的话说,“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思想,可以因为孤立独处而得到自由解放”c。 的确,孟子反复强调“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的东西,指的正是作为一个人成长初始条件的人之初的关系性。
这种由相互依存、内在和建构关系、共享价值、共同利益、群体责任、等级制度、差异不平等以及社会条件自由等因素组成的相关联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古代中国宇宙观所支撑的社群概念的基础。 西方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即便不具备负面含义,却也是不够积极的。 需要纪律、训练、努力和机会的人类生活的世俗发展过程,以及相应的人类不断进化的历史主义假设,都不是我们日常自我理解的一部分。 西方人似乎不加批判地致力于人类“生即为人”的“展现”概念,而不是“学以成人”的“建构”观念。
“展现”和“建构”之间的深层区别是两种文化理念的差异。 一种是源自古希腊的理念目的(eidos)和终极目标(telos)这样的回溯性概念假设,关于事物如何自然分类并展现成现在的状况。 另一种替代性的文化理念关注事物初始的前瞻性成长,关注如何在关系中实现富有积极意义的和谐,从而事物在此和谐化过程中成为与众不同的特色个体。 事实上,在中国宇宙观的语境中,域境中的个体的前瞻性成就要求仁与德这样的观念从出现的早期开始就朝着合一的方向发展,必须始终将其理解为独一无二的,并且只能通过关联的类比过程合成一类、一个范畴、一种普遍性。 认识不是从“类”开始的,而是定性地从引起共鸣、可以关联成“类”的特殊细节开始的。
为了把“学以成人”理解成某种建构性的替代概念,我们需要探索并接受中国古典宇宙观的三个条件:相互关联的关系性,通过实现有积极意义的关系的成长,以及在关系中实现的和谐——作为服务于其自身的个体化原则的独特性生发的来源。
七、关系的相互关联性 [12]
从经验的整体性和关系的建构性出发来看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所有活动都与环境相关,因此必然是相互关联的。 没有事情会自己发生,也没有事情是单方面或孤立发生的。 呼吸是肺与空气的交互作用,视觉是眼睛与阳光的交互作用,行走是腿脚与地面的交互作用。 毋庸置疑,“气”的宇宙观中所有概念术语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如天人、体用、变通、太极/无极、阴阳、道德、理气、无有等。 在这种宇宙观中,没有超绝的、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一”,也不存在基底的、原生的、本质主义的原则,更没有单一的超绝秩序。 正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及其他杰出汉学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所说,“中华智慧不需要上帝”a。
正如我们在强调“礼”时必须同步假定“乐”作为域境一样,在研究初始且独特的“性”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多层次的“情”景。 用“性情”来解析同一件事的时候,这个术语意味着两种不可分开的方法,即从特殊性的角度和域境的角度。 正是这种明确的相互关联性——即唐君毅的“一多不分观”——排除了自然类的存在,并且要求我们在情境中看待事物,同时又兼顾其独特性。 应根据具体事例进行归纳,而不是一开始就带着基本标准。 脱离具体域境的所谓独立的、本质的、天生的、完全相同的“性”是不存在的。
承认了“性情”等宇宙观术语是相关联的、互释的,实际上就要求我们始终将事物的域境作为其含义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加以考虑。 也就是说,要了解某人,我们必须了解其在关系网中的不同身份,如“兄弟”“阿姨”“老师”。 只有真正了解其角色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某人。 这种一贯有条件的、兼顾言外域境之意的认识论,假设其意义的源头是建构性的关系,那么这些持续变化的关系本身必然是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研学的对象。
虽然在我们熟悉的认识论话语体系中,“用事物本身的名称定义某物”要求在事件和其外表背后找到其必然的本质,来“理解、了解、知道、通达”。 但在中国宇宙观中获取知识的方式是“用事物的其他名称来定义该物”,首先要描绘出事件关系的域境。 对“性情”而言,除了可以提示我们初始情况的“性”之外,“情”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环境状况,可以告诉我们事物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认识到定性和定量的相互依赖关系时,“情况”或“事情”与“感情”之间的感知事实/价值的区别正在垮塌,所谓“客观”定量仅仅是对事物所在的差别关系域的一种抽象描述,这个关系场域定义着事物的独特性。
相似地,一个人到底是谁(情),取决于他具备的初始状态(性)的延展性(至大)和强度(至刚)的质的增长。
因此,在这种儒家的关系建构模型中,不是先有个人再有社群,而是因为个人与社群有效地关联,社群才成就了非凡与杰出的个体; 不是先有思想再有语言,而是因为人们彼此有效地交谈,变得志趣相投,家族才得以兴旺发达; 不是先有良心再有共情,而是因为真切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才团结成了一个自我约束、全心全意的社群。 a的确,一语双关——通过关联的生活方式来定义和实现的世界——是儒家在交流沟通的社群中创造积极意义的方式。
八、《孟子》与“学以成人”:通过实现有意义的关系而成长 [13]
倘若孟子真如人们所设想那样提出了一种更高级、实质性的人性观,那么,这种设想怎样与孟子所主张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协调一致呢? 他为什么要使用“端”这个词? 难道是指第一种模糊概念或迹象? 端倪? 萌芽? 我将论证《五行篇》和《孟子》提出的一个由关系建构的“学以成人”观念,这种观念看似悖论,需要用另一种格式塔来代替我们对于基本人性的既定概念。 我认为,与《孟子》一样,《五行篇》对于何以为人的理解是具有前瞻性、过程式、交互性且完全基于情境的,而不是回顾性、本质主义的。 问题是如何定义人类? 是对孤立因素进行猜测,还是在考虑初始条件的基础上分析出完整的后续行为?
由于对个体化和“自然类”有着常识性假设,人们往往不加批判地将其假定为一种对个人的默认解读。 这使得对《孟子》人性观的诠释似乎难以理解,而我将挑战这一难题。 下文将援引《五行篇》来确认孟子的“四端”是“成人”的初始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端”是与生俱来的。 但与此同时,类似“四行”那样的“四端”主要是由完全域境化的、关系中的、处于发展初期的人的习得条件所影响和建构的。
其中人的童年时的特点和意义并非源自家庭关系之外的天生“人”的虚构本质,而是来自真实家庭中相互关联的角色和关系。 说到相互关联的角色,比如有母亲就有孩子,有兄自然就有弟,有婴儿自然就有家庭圈子,家庭爱他们并使他们得以生存。 换言之,家庭的习性是抚养和教育婴儿的首要条件,婴儿的天然条件是次要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 “人性”最初主要来自家庭,它使人类得以成长,成为独特的个体,进而形成独特的人类。
在这种相互关联的意义上(如母女),人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是“拥有”或“加入”关系,而是被血缘纽带定位为大家庭中的对象,建构成不可化约的亲属关系。 事实上任何所谓的“个体性”,要么是从那些具体原生、最初获得的条件中抽象出来的,要么源自其关系网中获得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同样,任何“家庭”概念都是从具体的、特殊的人们(他们共同地、有机地构成了一个人类的关系矩阵)中抽象出来的。 特殊的人们和特殊的家庭都是特殊关系的具体配置,并且彼此均处于焦点—场域(心—场)关系之中。
杜威认为必须有成长:“我们生来便是与他人关联的有机体,但并非生来就是社群的成员。 ”b“四端”并非全人类的前社会的、天生的性质。 但是,它们仍然是早期的初始条件。 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相关联生活可依赖的开端,需要培养生发,以使人们成为家庭和社群中积极的、完美的参与者。 它们描述了人类在伦理、美学、认知和宗教方面的特殊开端,由此便出现了人类。 儒家的愿景和计划则是将不成熟的、但有机地相互依存的人纳入家庭关系网,并将他们转变为在一个蓬勃发展的精神社会中的热心参与者。
九、了解“潜在可能”:成就和谐关系 [14]
换句话说,“成人”的“潜能”不仅仅是最初的端倪,更不是家庭关系之外的天生“人”的虚构本质。 相反,某个人的“潜能”事实上是从具体的、随机的互动中同步地浮现出来的,最终成就一个特殊家庭中的个体。 因此,对“潜能”的正确理解是,它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演化,而不是前置于环境。 对于关系中的人而言,“潜能”始终是独特的,而不是通用的或普世的,并且只能在特殊叙事中展开之后才为人所知,“潜能”不是作为一种天生固有的、决定性的禀赋而存在。 a因此,我的论点是,仁义礼智作为“人性”内涵的主体来自后天习得,而不是上天赋予。 与“仁”相似,“性”不是本质的或上天赋予的。 两者都既是来源,又是产物,即初步的原生条件和适应性的可靠结果。
“性”是一个可变因素,取决于一个人的出生家庭。 如果这个家庭道德高尚,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那么就有较多有利资源可以积极影响到这个新生人; 如果家境窘迫,困难多多,那么这个新人所面临的便是一条更加艰难的成长之路。 但是,即使舜出生在父亲是瞽叟之如此不利的家庭环境中,尧的榜样作为文化资源仍然可以积极影响舜,促使舜也成为圣人。 尧的积极作用恰好说明,总有一些文化资源可供汲取,可以帮助有志新人“学以成圣”。
《孟子》用人们熟知的园艺和耕作来打比方——知“根”——即加强对作物和动物生长之“本”的设想,或者说实现它们的内在潜能。 但是,园艺耕作与狩猎采集之所以不同,恰恰在于前者对人工环境和劳动力集中的依赖。 实际上,本性的实现依赖于栽培和情境,否则,几乎所有的苹果都会变成肥料,橡子会成为松鼠的食物,鸡蛋都会成为蛋卷。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uebaoqk.com/xblw/6211.html
《“学以成人”:论儒学对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