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咨询服务正当时学报期刊咨询网是专业的学术咨询服务平台!
发布时间:2018-06-05 16:3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下面文章主要以黎紫书作品中体现的哥特式特征开始分析,发现黎紫书笔下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黎紫书的创作对于哥特文学具象化也是一种传承,也充分反映出了人们的心理,而黎紫书的哥特式文化幻想对于现代现实世界也具有正面指导意义,黎紫书小说创作也赋予
下面文章主要以黎紫书作品中体现的哥特式特征开始分析,发现黎紫书笔下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黎紫书的创作对于哥特文学具象化也是一种传承,也充分反映出了人们的心理,而黎紫书的哥特式文化幻想对于现代现实世界也具有正面指导意义,黎紫书小说创作也赋予了传统哥特模式多样化现代化特征。
关键词:黎紫书,哥特式,现代焦虑,空间,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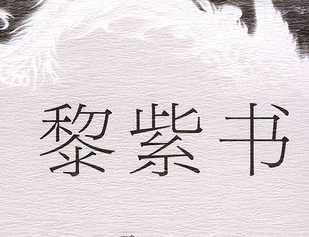
黎紫书曾被黄锦树誉为“自有马华文学以来最大的传奇”①。其“传奇性”不仅在于她自学成才且获奖无数,更在于作者不拘囿于传统成规,而于横贯古今的时间脉络中谱写出各式各样的人、情、世、故。然而正如王德威所评述,“营造一种浓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戏”②,黎紫书小说中的历史回忆和现世人生,都仅仅是展示人世生存的阴暗与沉闷,以及人性隅角中的欲望与恐惧的试验场。在她笔下,世界阴冷而黑暗,不同时代的底层华人始终受制于性别、身份、历史和文化的规范界限;人物生存于文明与野蛮、真实与虚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危险阈限,萎缩而压抑的身心皆被欲望和焦虑所侵占。最终,人物或以暴力和死亡突破困境,造成更加残忍血腥的罪恶,或是无奈地选择隐忍和逃离,企图寻获救赎之路,却诡异地导向心灵的放逐和空虚。
一、封闭中的压抑:空间意象的哥特式呈现
英国评论家克里斯·鲍迪克认为,哥特式文本必然包含“封闭空间中的幽闭恐怖感所引发的恐惧心理”④。传统哥特文学以幽灵古堡式封闭空间设置为核心,营造出典型的哥特式阴暗恐怖氛围,以此对应人物在焦虑性生存处境中饱含压抑和恐惧的内心情感。可以说,心灵与世界相互映照、互为镜像所展露的黑暗与恐怖是古老哥特文学传统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黎紫书小说中的空间场景和人物内心呈现出明显的哥特式风格,几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阴暗压抑的封闭式环境中。人物长期身处充满窒息感的哥特式空间,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自闭倾向,或不可自拔地沉溺于黑暗幻想。例如,作者最擅长以带有家庭内部特征的空間设置来展开情节,将常规思维中阳光普照的家庭空间塑造成阴暗、压抑,甚至充斥死亡气息的危险之地,从而对家庭成员造成身心的双重威胁。
在《告别的年代》中,主人公“你”长期独居在“坟塚”般阴森破旧的五月花旅馆301室。闭塞阴暗的生活空间几乎隔绝了主人公与外界的接触,人物终日沉浸在关于死亡的回忆中无法自拔。小说一开始便以诸多细节描述五月花旅馆的阴森诡异氛围:“每一间房都像盘绕着阴魂似的,充满了不属于人间的杂音和气味。楼梯像通了灵,脚还没真踏上去就听见木板的呻吟……”⑤这种带有死亡、压抑气质的空间便是传统哥特小说中幽灵古堡的当代变体。另外,作者还着重于突出家庭空间由于隔绝隐蔽而产生的危险性。家的四壁遮挡了外界视线,家庭成员可以在封闭空间中暴露自身,这往往促使家沦为罪恶滋生之处,令人瞠目结舌的罪行在“家”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蔓延、泛滥。在《蛆魇》中,黎紫书直接暴露了一个古老家庭内部的极端阴暗和罪恶。白蚁肆虐的破败古宅充斥溃烂腐朽的气味,家庭成员相继陷入自闭或疯癫状态,他们互相迫害甚至残杀,黑色罪孽如同白蚁,侵噬进家庭的每一道缝隙。
正如经典哥特文本中幽灵古堡引发人物的恐怖心理,黎紫书笔下的封闭式家庭空间已成为人物欲望与恐惧的主要来源。生存空间的特征映射在居住者心灵中,从而造成其内心的压抑、焦虑与恐惧。关于这种外在空间对内心空间的塑形和规训,福柯在《另类空间》一文中有所阐述:“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⑥在福柯看来,空间承载着文化政治内涵,是社会权力运作的场域。人类置身于空间场所之中,无时无刻不承受其无处不在的塑形力量。例如,对黎紫书小说中的大多女性而言,“家”常常扮演着双面角色:既是抵抗外界侵袭的堡垒,更是禁锢和规训她们的监狱,且这种对女性身心的操控和宰制主要源于家中的男性权威。它占据、统治并扩展男性空间,使权力控制之下的女性不断压缩自身生存空间,直致退缩到完全封闭的内心空间之中。
以《赘》为例,小说以家庭主妇静芳的瘦身诉求对比“贪吃”心理贯穿始终。静芳在厨房杯盘碗碟间的流连和对家中食物的不舍,不仅在表层上揭示她婚后始终赘肉一身的原因,还深刻反映出女性受制于家庭权力结构而压抑自我意识的生存现状。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⑦在家庭空间结构中,厨房无疑是艰辛之所,并直指家中的屈从地位。一般而言,厨房总是女性的空间,是女性“接纳父权制的最佳场所”⑧。
由于常年被困锁在厨房这一家庭空间的边缘,静芳对于自己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式角色定位已远远超越自己的爱美天性,进而塑造了她压抑自身渴望而屈从于家庭男性权威的内心状态。在小说末尾,静芳萌生“死于水中”的心愿,渴望以水来压缩多余的肉身,事实上这是其内心极度萎缩压抑的表现。在黎紫书笔下,由于常年受制于家中男性权威,众多带有自闭倾向的女性纷纷无限压缩自己精神与行动的地盘,无一不龟缩在自己封闭的内心世界。这其实是女性无力和绝望心理的展露,也是女性生存困境的微缩写照。
另外,梦境是另一个体现人物内心压抑状态的表现形式,是本不可呈现的内心空间的具象展示。黎紫书小说里遍布梦境以及意识流动的幻想书写。在空间权力争夺中落败的主人公们面对现实生存空间的日益萎缩,出于逃避或抵抗心态,纷纷自现实生存空间逃逸而出,遁入自己以梦幻形式建构的内心空间。然而作为生存空间的外向镜射,体现人物内心空间的梦境无数次出现死亡、囚困和逃离的意象,同样呈现出极度压抑不安的空间特点。作者其实是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以更加荒诞阴暗的心理幻想反映人物生存状态的恶劣。如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展露了极其精妙的虚实互涉手法。
现实中,主人公“你”自小跟随妓女身份的母亲奔波迁徙于各个破旧旅馆,从未拥有过固定的栖身之所。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声称:“一切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具备家宅概念的本质。”⑨但居住者首先要形成家的认同感。然而生存空间的轮番更换,以及要和众多陌生人在空间中“共享”唯一至亲的事实,早已使“你”失去了家的归属感。因此,在母亲病逝后,梦境成了寄人篱下的主人公寻求庇护的唯一内心屏障。在“你”的梦境中,无数次出现迷宫、回廊、高耸的螺旋梯等空间结构意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没有出口、没有尽头,呈封闭状态。另外,梦境中还经常出现“门”的意象,门本身象征空间的封锁,“打开门”才意味着寻获出口。主人公反复梦见自己抓住把手企图把门打开,这可视为他企图逃离的内心诉求。
二、边界上的焦虑:现代生存的哥特式特征
在黎紫书小说中,封闭性生存环境中的人物似乎患有“幽闭恐惧症”:他们因外在权力空间的压迫和宰制而渴望独立的“个人空间”,却又在封闭空间中时刻感受到心灵中波涛汹涌的欲望与恐惧。内在的“异动”使得原本封闭而稳定的内心出现龟裂,呈现极度压抑又欲冲破禁錮的阈限性焦虑。这种内心空间的濒临崩溃往往预示人物对规范性边界的突破行为,原先边界所维护的空间秩序随之面临瓦解的危险。黎紫书小说中众多表面看似稳固封闭的生存空间,事实上都蕴含着不稳定性,居住者置身于道德与非道德、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性边界,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汇点。在这个阈限性空间,各种异形力量入侵边界,出没于人物的住所,占据他们的灵魂,致使人物产生导向失控的焦虑与恐惧。
由第一部分论述可见,在黎紫书笔下,家已成为最主要的威胁来源。就象征意义而言,家庭结构秩序是社会文化自我组织的法权基础的微缩化和具体化体现:这些法限定了社会权力、道德、行为等诸多准则的边界。通过划定界限,社会宣布中心与边缘,合法与非法,正常与疯癫的区分。黎紫书以个别化的家庭叙事唤起人们对于社会文化性边界的注意和思考,譬如规定家庭权力结构的“父的法权”。冰冷而压抑的家中通常充斥着父权制结构,众多自然意象诸如黑夜、圆月、狂风暴雨等往往象征混乱的女性冲击力量。和作为“边缘性文类”的哥特文学一样,“‘女性’是西方文化中最强大、最恒久的‘他者’”{12}。她们生活于父权边界之内,出于自我保存意识而心生焦虑与恐惧,而她们对边界的意识和反抗也形成对家本身的威胁。女性和男性宗法秩序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家的不安全性。
黎紫书在《告别的年代》中完整呈现了一个男权结构家庭中的女性由无奈压抑到意识性反抗,并最终颠覆原有家庭空间秩序的过程。身份低微的戏院售票小姐杜丽安因机缘巧合被黑道角头钢波所救,嫁为继室,进入了这个以丈夫为权力顶点的父权制家庭。金字塔顶之下是与杜丽安年龄相差无几的继子继女,杜丽安最初只是乞求融入这个家庭结构的“外来者”。弗洛伊德通过哥特文本分析“诡异”(the uncanny)时指出,诡异体验往往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
原本熟悉的家庭空间中萌生诡异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存在威胁原有空间秩序的“他者”。哥特模式一方面揭示了父权制基本准则中的权利不均: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是极度区分的,男性占据绝对优势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表达了内在于西方父权制前提中的恐怖,即女性是极具威胁性的“他者”,她们对父权制家庭空间的各种边界形成冲击,从而使原本安定的家庭空间产生哥特式恐惧。
在小说中,杜丽安是凭借“走出家庭”并掌握经济权的方式逐渐打破家庭空间的权力划分。杜丽安开设茶馆谋以生计,从此由他人口中的“大嫂”摇身变成“老板娘”、“丽姐”。称呼变化对应身份转变。杜丽安由原先依附家庭和丈夫的“妻子”角色,转化为精神独立的个体,其个人价值已不仅仅由家庭权力结构所决定。然而,妾室身份意味着她仍然被排斥在家庭结构之外,这一点在杜丽安重置新居却不能供奉夫家祖先灵位时有所暗示。
正妻家中已供奉夫家历代祖先,这表示她不是刘家人;自己家中不能供奉杜家祖宗,因为她已是嫁出杜家的女儿。杜丽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问题:“那我是谁啊?……既不是杜家女儿,也不是刘家的人。”{13}显然,此时的杜丽安仍被传统父权思想所禁锢,困陷于家庭身份之中,但质疑的产生往往预示着超越界限的可能性。最后杜丽安如愿以偿地在家中供奉杜家祖先,象征其彻底颠覆原有家庭结构,重新建立了新的家庭秩序。
黎紫书小说的家庭伦理主题主要描绘了女性受困于父权制边界以及逾越边界的家庭悲喜剧。而作者对历史题材的书写,则着力于表达新一代华人在历史文化承袭过程中产生的断裂感与困惑感:他们与先辈华人之间已划下一道深刻的历史文化界限,然而这并不是一条明晰稳固的边界。在作者看来,华族历史与过去罪孽并不会销声匿迹,而是如同无法破除的哥特式诅咒,世世代代纠缠人物的心灵。哥特式恐惧已不仅仅存在于密室般的幽闭空间,创伤性的过去将心灵本身塑造成囚牢。这为黎紫书追溯华人过去、确认华族身份的历史小说抹上极为浓重的宿命色彩。《国北边陲》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文本,小说以一个受到“死亡诅咒”的家族寻找解药的传奇性故事来隐喻马来西亚华人始终背负“寻根”使命的历史和现实。
家族古老的“死亡诅咒”起源于主人公曾祖父初入异境山林时误食一只奇兽,此后,传说中的解药“龙舌觅”成为他们家族的图腾,而“‘寻找’遂成为陈家后裔的人生命题”{14}。虽然主人公最终寻获神草,企图渡过被诅咒的30岁大限,却惊愕地发现“龙舌觅”是没有根的,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根据记载,患者需食用神草根部才能获得疗效,即意味着根本没有扭转家族宿命的方法。这个“死亡诅咒”如同伊甸园神话中始祖原罪的变相隐喻,永远无法被避免和断绝。
在《国北边陲》中出现了“诅咒”这一经典哥特元素。作者运用“家族诅咒”意象为代表的过去神秘性构成哥特式超自然的核心,贯穿小说始终。背井离乡、远渡南洋的华族祖先由于吞噬代表异域文化的“奇兽”而受到诅咒,如若无法找到“神草”之根,整个家族将无以为继。这象征着流落异域、与异族交融的华族在接收异域文化过程中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文化历史渊源。然而,深入骨髓的“寻根意识”从未在华族成员心中消失,这种人生主题如同幽魂一般不断在华族后代子孙的生命中出场,因为祖辈的文化渊源永远是后辈身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漫长的时间间隔和广阔的地域分离已造成文化渊源的陌生性和模糊性,这也成为新一代华族成员内心不断滋生身份焦虑的源头。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同样探索了这种文化寻根和身份确认的主题。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杜丽安,还是90年代的少年“你”,他們都因遗失身份根源而焦虑不安,皆困陷于过去对现在的纠缠而无法真正“告别”。“本应该被隐藏掩埋,却被直接公开”{15}的过去强制性重现成为了人物内心诡异的核心,它向人物展示某种过去非常熟悉,现在却感觉极度陌生的事物。正是这种过去与现在之间相互区分又界限模糊的状态成为了人物心生焦虑的主要原因。
善恶斗争是传统哥特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通过惩恶扬善,哥特文学获得了自身的社会性价值意义。但在黎紫书的作品中,罪恶具备了原罪式的永恒性。凭借在文本中建构“罪恶轮回”,不断上演由“逃离”到“逃向”犯罪的诡异转变,作者展示了生存困境并质疑人类救赎的可能性:“人们无需体验,无需证明,却只能接受和不断地洗刷罪孽”{16},拯救之途仍漫无止境。
三、越界的恐怖:失控人性的哥特式书写
上文分别论述了黎紫书作品中出现的哥特式封闭空间意象,以及左右人物生存空间秩序和心灵稳定性的象征性边界。边界意味着“禁止”或“禁忌”,而禁忌通常与欲望冲动相关,边界存在本身就为其所界限之物的越界性犯罪行为提供目标和前提。这种对罪恶的趋向性被庞特称为哥特模式的最终目标:“一切哥特都是关于取缔更迭,关于超越的意愿,以及争取完全免于法律支配的幻想。”{17}事实上,哥特式小说历来被称为“禁忌和犯罪的文学”{18},它所强调的非理性冲动和破坏最初便是18世纪这棵扎根于理性思维掌握世界的启蒙之树上所结出的“恶果”。
哥特天生固有一种打破固定和封禁的“流动性”、反叛性精神:它展露以上帝为原型塑造而成的“完美”人类所忽视的无意识领域,揭示被光明而美好的世界所遮蔽的阴暗角落。西方世界自启蒙时期以来创造了所谓“人类”以及各种关于“美好世界”的定义。而定义即是划定边界,即是封闭性空间。传统哥特文学以塑造弗兰肯斯坦式怪物形象和摧毁封闭空间之墙的隐喻方式,暴露理性定义之内所隐藏的非理性阴暗,特别是人性和生存的黑暗侧面。
与此类似,黎紫书在小说中塑造了各种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并在压抑恐怖的文本氛围中,使各类怀有阴郁诡异心灵的哥特式人物粉墨登场。栖居者出于本能的生存欲望将“兽性”一面充分展现:通过失控般的血腥暴力打破法律、伦理、宗教等禁忌性边界,从而突显心灵深处源于非理性的易罪冲动。如前文所述,哥特形态最初是作为对启蒙理性的回击而出现在作品中。
没有启蒙之光的普照,非理性和超自然仍然与早期以神话和迷信思想为基础的原始世界和谐共存,并不会成为现实性语境空间中诡异恐怖的怪物。哥特拒斥启蒙理性建构定义性的概念分类,特别是关于“人”的分类思想,这种分类以权力空间化的手段将其他不符合标准定义的种系驱逐到禁闭性空间,譬如社会上的疯人院、监狱,乃至家庭。就文化层面而言,定义之外的非标准人类则成为了“他者”,是未知的危险所在。
女性作为“他者”最典型的代表,到了黎紫书笔下已迥异于传统东方文化中娴静温婉的形象。除了以非道德手段摧毁父权家庭秩序的杜丽安,众多女性人物纷纷以精神上的疯癫或行为上的暴力,沦为传统视角下的“怪物”。如《有天使走过的街道》中终日坐守窗口窥视路人、沉浸在欲望幻想中的疯妇,以及《蛆魇》中不堪忍受母亲偷情事实、以暴力性幻想进行反抗的女儿:“午夜,一个披着雨衣的男人冲进屋子里,手里抓住一把斧头。
……他像狂风那样席卷进来,把躺在沙发上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一手揪起。……看见一对裸身男女霍地从床上弹起。……朝着那惊慌寻找遮掩的女人冷笑。”{19}这个暴力捉奸场景的幻觉反映了女儿的内心愤懑以及按捺已久的报复心理。通过疯狂暴力的精神幻想,人物内心积压的焦虑、恐惧得以释放,从而获得某种慰藉与快感。
而那些长期遭受父权压制的女性一旦决心反抗,常常会以最血腥的暴力行为报复甚至弑杀欺压她们的男性权威。《推开阁楼之窗》仅就标题便使读者联想到经典哥特式小说《简·爱》中塑造的被男主人公囚禁于阁楼、最终逃离并焚毁囚牢的疯女人。主人公小爱为了逃离家庭阴影和继父控制,不惜残忍地将自己刚生下的婴儿溺死在马桶里;《我们一起看饭岛爱》中的未婚先孕后被丈夫抛弃的素珠也曾出于报复而意图将自己的孩子掐死;《把她写进小说里》中江九嫂可谓作者笔下最具有邪恶女巫气质、对待男性最为暴烈的女性。她曾持木棍如同讨债厉鬼般追踪抛妻弃子的弟弟,曾半夜持尖刀追杀凌辱妹妹的叔叔,还曾生生打断懦弱丈夫的右腿,把他赶出家门。
作者以后设手法如此描述:“江九嫂将如幽灵一般长期蛰居在黑暗中,……她的阴沉的个性狠辣的心肠也许就在无边无尽的黑暗中丛生与成长。”{20}这些邪恶的女性人物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传统哥特文学中的女巫、恶人和怪物形象,其暴力性甚至较男性人物更加血腥残忍。作者在狂欢般的暴力叙事中展示了女性突破父权秩序与伦理边界的释放性快意。但这种女性暴力化甚至怪物化同样显示了传统女性活在父权秩序宰制之下的悲哀。她们居于家中一隅,压抑萎缩在无声的内心空间,是家中男性一再的缺席和欺压激发她们难以抑制的焦虑与愤怒。这些女性人物如同怪物般的狂躁乖戾以及血腥暴力其实是女性寻求声音和权利而身体力行的抗议。
可见,不同于传统哥特模式以怪物外在化、异常化的恐怖,象征性隐喻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欲望,黎紫书着力于刻画众多普通人物甚至正面人物的内在残缺与行为暴力,这便使小说中的哥特式恐惧更加触目惊心。对于哥特模式而言,怪物的重要性在于它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它们“起到定义和建构‘标准’的作用。……负责管辖人类的边界,并指明那些不可逾越的界限。”{21}而在黎紫书笔下,怪物已非传统范畴中可怕的特定形象,而是深藏于所有人的无意识深渊,造成心灵的分裂,迫使哥特式主体挣扎于理智与疯癫、人与非人的边界。
这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怪物也被称作“异己”,是“第二个自我的呈现,或一个与个体密切关联的他者和自恋镜射的原型”{22}。黎紫书主要以“理想自我”与黑暗“他性”的对比冲突来突显“异己”存在的普遍性。通过探索那些逾越宗教、道德等标准界限的“非人性”异己,作者反证那些所谓的“怪物”同样拥有“人性”,从而显露对于提供某些宗教教义或道德基准的宏大叙事的怀疑。
书写人类原始欲望对宗教教义及其神圣性的冲击和解构是黎紫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在黎紫书笔下,绝大多数信徒甚至牧师往往扮演着诱惑者、出轨者、淫乱者等形象,人物屈服于内心本能欲望而一再跨越宗教教义和善恶道义的边界,使得原本圣洁的宗教也沦为展现人性腐朽与丑陋一面的试验场。在《天国之门》中,黎紫书在表层上叙述了一位道貌岸然的圣职人员的荒唐行径,在深层次里则毫不留情地鞭笞神圣宗教帷幔遮掩之下人类屈服于本能欲望的腐化堕落。作者选择一个正面人物形象来揭露人类对本能欲望的放纵、对神圣天职的亵渎,将人物身上可能反映出的人性虚伪、丑恶一面刻画到极致,从而引起读者对于人性纯洁以及宗教救赎可能性的怀疑。
在小说中,作者以象征罪恶源头的“苹果”意象贯穿始终,甚至连主人公洁净躯体的香皂都散發着苹果的气味,这象征人类始祖被恶魔引诱而偷吃禁果之后,劣根已深埋心中,渗透进生命的每一寸呼吸,使人常常“像野兽一样原始而焦虑的喘气”{23}。人活于世,虽然还保有依照上帝形象而仿造的肉身,仍然善于以各种方式洁净躯体,但灵魂的另一半已无可救药地糜烂和背叛;虽然在宗教包装之下外表看来还是个正人君子,但已经无法断绝心灵中扎根生长的恶性,亦无法阻止徐徐下坠的生命姿态和趋势。
而在《流年》中,作者对社会公认的道德典范进行批判。年少丧父的花季少女纪晓雅在温文儒雅的书法老师庄望身上寻找理想父亲的影子。然而温柔体贴、外型美好的庄望老师却拥有强烈恋童癖好,在教书育人的神圣知识殿堂里引诱女学生,上演一幕幕师生恋情。最后,庄望老师因为不断的淫乱荒唐行为而被调离学校,这无疑是对教师这一社会公认的道德典范形象的消解。另外,黎紫书笔下诸多的“丑父”、“恶母”“背叛的革命者”等形象皆是对于传统正面形象的负面性解构,是“异己”形象的隐喻。
在这里,黎紫书主要通过将怪物“内在化”来突显哥特式“异己”主题。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我们是自身的外国人,我们是分裂的。”{24}在自我与异己之间的边界性阈限,心灵黑暗侧面所有的憎恶、贪婪和偏见赤裸裸地上演,使人性摇摆于善与恶、正与邪、文明与野蛮的两极之间,从而一再模糊了“人—怪物”的范畴边界。
结语
黎紫书通过描绘小说人物濒临崩溃的心灵空间和异动不安的生存处境,创造了一个充满压抑、焦虑和恐惧的黑暗文学世界。通过强调边界存在,作者突显既定现实的无限性和流动性,以此动摇了诸多社会公认的二元对立性范畴。又通过书写被长期压抑和掩盖在文明表象之下的阴暗、丑恶与罪孽,揭示了那些一直以来被理性所否认和隔离的“异常”,其实早已渗透进人类自身和社会文化的各方各面,成为其固有部分。黎紫书在小说创作中展示了不畏丑恶、直面阴暗的揭露和颠覆意识,体现了哥特文学创作的精神所在:“以过度的情感联系崇高,去探索我们难以解释的生存中那些不可言说的事实。”{25}
这也是当代社会仍然需要古老哥特模式的主要原因,迫使读者面对许多平日避之不及的黑暗,启发他们去质疑自身,以及周围这个所谓秩序世界中的不公与偏见。通过对于“非理性”、“非现实性”和“非道德性”的描绘,黎紫书展示了阳光普照背后“怪物”横行的“畸形”阴暗世界,在那里,所有既定成规的现实概念都沾染了黑暗和犯罪的恐怖阴影,从而引起人们对于理性光照之下的阴影空间以更多的关注与仁爱。
综上所述,黎紫书借助哥特元素与形式探索现代主题的小说创作,无疑对哥特形态与当代主题的结合,对传统哥特模式的多样化和现代化革新具有突出贡献。她丰富了哥特式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使长期以来学界定性评价中形式刻板、手法固定的哥特体裁,在应对新时期的性别、身份和历史等全球性问题时,彰显出哥特文学样式的优越性以及哥特式精神内涵的深刻性。作为一个在小说实践探索上不断推陈出新,在直面和揭露社会与人性的阴暗面时始终鼓足勇气的年轻作家,黎紫书即使已经度过自己“花踪明星”的辉煌时代,仍将有更漫长的文学创作之路要走,相信那将是一个值得读者期许的未来。
相关阅读: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
自从清朝的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改革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自此华夏民族开始了严峻的挑战。同时我国的民族文学也受到了相应的发展危机,在患难当头,我国文化人士应该坚持不屈不挠的斗志,为国家的民族振兴而奋斗,需要对中国文学进行重塑,发展了一个世纪历程的近代民族文学,和近代国情发展相结合,和文化共同进步,才能获得自救与求生。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uebaoqk.com/xblw/3482.html
《黎紫书作品中哥特式焦虑形态的展现》